“白马和银枪”---我的北大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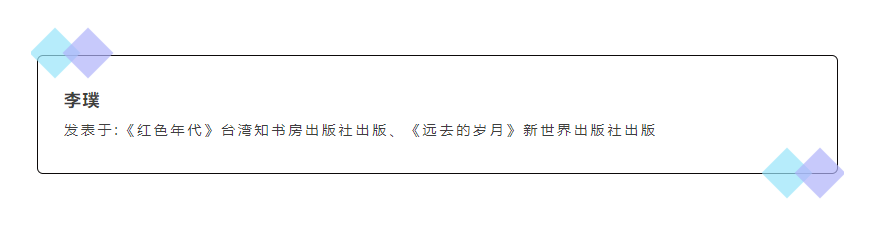
“再上征途”

路漫漫
1968年6月18日,毛主席批准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开始。已经改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三十一团四连的曙光四队,来了大批哈尔滨知青,农垦战士变成了兵团战士,我们也被尊称为“老六”知青了。我且没感到先行者的骄傲,我们自愿下乡时想的是来上课,取得毕业证,再回城升学,现在看来这个课是没有毕业的时候了,就这样真当个农民吗?转眼已快20岁了, 20岁,岳飞已枪挑小梁王、罗成16岁破长蛇阵、邹容18岁发表“革命军”、聂耳作国歌也只有23岁……,我的“白马”、“银枪”呢?
兵团组建六师,三十一团要承建六十一团的三个连,地点在抚远。那地方靠边境,可不能去,要是和苏联打起仗来就是前线、那是从无人烟的大荒原,还是沼泽地,人要不小心陷下去就没命,越使劲拔腿,陷得越深,救你的人也会跟着没命、那里更冷,这大冬天去了吃什么?喝水只能化冰雪。听到这些议论,我好像又一次看到了天机,荒、苦、危险正是吸引我的地方。少年有志各不同,还看时事论英雄,去更广阔的天地,寻找“白马”,打造“银枪”,我又一次主动要求,自愿去开发抚远荒原。
曙光农场、四队是我走上社会的起点,是我人生的梦开始的地方。那白云、白雪、顺山倒喊声中的白桦;那红旗、红语录、红头巾;那绿山、绿野、绿军装;那蓝天、蓝水、蓝套袖;那金色的阳光、金色的麦浪、金色的梦;那激情、友情、纯情;那真诚、宽容、关爱。那些人:幽默的国民党特务杨兴宇、宋木匠、老班长张传新、知识渊博的马南祥、懒滑的张永兰、小辣椒、左寡妇、年轻的军代表、戴成章队长、陶队长、胡会计、兽医孙伟、当过土匪的高秃爪子、神秘的五保单身老寇头、传曾给座山雕谢文东管过事的老钟头和女儿钟万香、小九子、王华子、张士林、刘世玉、刘世堂……,当然还有那些和我同到四队的十一名知青同伴及后来的大批哈尔滨知青;那些事:……,都深深地沉淀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最美好的时光。
“初踏大荒”

我们是坐着爬犁,拖拉机拉着,顺着新修建不久的二抚战备路,顶着大烟泡进入荒原的。风雪刮得什么也看不见,听到风吼声中不时传来几声凄凉的乌鸦叫,狗皮帽子上结满了白霜和冰,得经常下来抖掉身上的雪,跟着爬犁跑上几步,领略大荒原的威风外,什么也没有看到。
三天的大烟泡过后,我钻出帐篷,适应了耀眼的光芒,睁开了眼睛,青天白雪,没有山没有云,也没有风。一望无边的蓝和白充满整个世界,天边的地平线竟然和大海一样是弧形的直接苍穹。远处融入蓝白间的淡灰玫瑰色是白桦林,林中垂直升起邻队的炊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可改为大荒孤烟直,长空唱雪白或雪原伴蓝天了。我们博大的文化中有许多形容山雄壮、海辽阔的优美词语,但在我浅薄的学识中找不到一句形容大荒雪原的词句,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写的也是秦晋高原,这里也并不是惟余茫茫,还有那碧蓝的天空呢。我头脑中更创造不出一句词语,能够形容这一刻我对北大荒之壮美的感受。陶醉中,我仿佛看见了“白马银枪小罗成”,在这白地蓝天中“闯关叫阵”。(为了表达这种感受,后来我发明了流彩画,我的画作中喜欢使用纯蓝色和粉红色就是源于这一刻吧。)
激情不减的我,夜不眠,躲一躲烤乌拉草鞋垫的味道,出外换气。黑夜奇冷无风,天上的星星比任何地方看到的都多,好像都冻在了空中,和我一样索索发抖,只是星更高,宇宙更神秘深远,真是穹宇浩瀚,还有苍凉。一颗流星划过,远处传来低沉的狼嗥。
开春,雪逐渐溶化,北大荒露了真容。荒原原来是由无数塔头墩子组成的,塔头墩子长在表面看不见的烂泥中,这就是沼泽地。要踩着塔头墩子行走,否则踩进泥泽真的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长出野草后,是美丽的绿色大荒原了,采摘黄花菜时更要踩准塔头。
伐木、打井、脱坯、盖房、开荒、种田,我们踏出了荒原上的第一道脚印,拖拉机工作3小时拓开了第一道田垄,这个长度的田垄是不是世界之最?我不知道。
不久传来友团的拖拉机陷没沼泽的事,第一道脚印是伴随着危险和牺牲的光荣。
我这样记载了我心中的北大荒:
盘古开天定八方,独留神异北大荒。
千年苍海人踪绝,乾宇云飞万里扬。
老树深山泽鱼跃,獐狍熊鹿浩原忙。
雁过长昊炊烟直,夜静星高走群狼。
百谷欢歌生黑土,绿盛春夏唱秋黄。
严冬白雪伴冰洁,刺骨寒风壮尔郎。
放眼弧形地平线,忽闻阵阵野花香。
桦林醉倒多情汉,笑醒不知梦哪乡。
后来我的这几句顺口溜,还被哈尔滨电视台制作成了歌曲:“初踏北大荒”,由李利作曲,岳世一娃演唱,成为我的专题片“写在大地和蓝天上的流彩人生”的主题歌。
“荒原熊祭”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两句话是对北大荒的荒凉和富饶最经典的概括。但野鸡并没有飞到六十一团五连的饭锅里,化开的雪水里也闻不到鱼味,冒着热气的萝卜汤总要细心挑净漂浮的蚊虫,才能入口,有时可见到三俩成群的狍子,没试过用棒子能否打到。
一天早上6点多,宋指导员喊,拿家伙紧急集合,我们拿起随手的锹镐匆忙跑出帐篷,有人连棉裤都穿反了。见不远处,雪地里有一只黑熊行走,大家兴奋的呼喊着追赶,黑熊不紧不慢地越跑越远。两台东方红拖拉机启动了,半个小时后轰鸣的拖拉机拖着一只和链轨一样长的黑熊凯旋了。几位英雄兴奋的讲诉:如何机智地拦阻不让黑熊跑入桦树林,追赶得它跑不动了,拖拉机从黑熊身上压过去,黑熊起来还跑,又压上去,停在黑熊身上,那黑熊还扑打着链轨,另一台拖拉机压上黑熊的头……。
面对一碗热腾腾的熊肉时,我眼前总闪现黑熊在雪地上奔走的情景,那跃动的黑点,像不断变动位置的音符,在一片雪白中画出的单调曲线,是生命的进行曲,还是挽歌?
这熊肉比牛肉粗、据说吃了后背都会透油、这是难得的口福,听到这些议论,很偏食的我还是放嘴里一块熊肉,咽了一小口,一阵恶心全吐了出来,多少天我都觉得后背有透油的感觉。看着外面晾着的熊皮,我不解熊应该冬眠的,何以这么早就出来了?
小时候,我和弟弟养了一只小鸡雏,成了弟弟的宠物,长到九斤,就叫九斤黄,是大院里的鸡王,我还画过它站在弟弟肩上的速写,后来它被做成了鸡炖蘑菇,我和弟弟都一口没吃,至今都不吃鸡肉。
弱肉强食的道理,是生命体的本能吗?我弄不明白。
“千钧井绳”
连里唯一的水井,在离井口约两米的地方冰越结越厚,打水桶已不能通过了。傍晚我们班去除冰,把井绳结成一个U形套,人一只腿伸入套中,顺井绳滑下去,骑挎在井绳上,双手用斧子刨冰。天太冷,大家轮流下井,也只能坚持几分钟。轮到我下井了,为了手灵活,我只戴了线手套就顺井绳滑下,黑暗中腿且没能伸入绳套,以致滑了下去,幸好抓住了绳套才没有掉进井水里,井口结冰处以下是空旷的,我伸腿也够不着井壁,悬在了半空,只靠两手抓住井绳。可能是手僵冷和慌张,手感到越来越没劲了,无力向上攀爬,体操队练就的拔起技巧一点也用不上了。别慌,抓住别松手,我来了,上面传来了老班长张宪克的山东口音。他不顾井壁冰滑,两脚蹬着冰壁, 一手揽着井绳,一步步地下来了,伸出一只手,抓住我的手,用力把我拉到了冰口上来。那一刻我感到那只手那么坚强有力,那是一只可以依靠的希望的手。
普通农业工人、我们老班长的手,和天安门上挥动着力挽历史狂澜的巨手一样伟大。
老班长何时仙去,我且不知,很是遗憾,在天堂的这两只手是否有机会握在一起了?
“放映员跡”

1969年底,团里人陪慰问团来五连慰问,发现我写的空心字口号和黑板报美术字写画得好,文化干事幺万和把我调到了算我俩人的团电影队。
我第一次独立放电影是到两个伐木点。带着8.75毫米放映机和小发电机,搭车队拉木头的大挂车先到了210公里伐木点,放映前还磕磕巴巴的宣传几句,得到了掌声。要到194公里四连伐木点去时,团里的挂车司机谁都不去,因为是计件拉运,谁也不愿意浪费时间和多跑路。这时我完全可以不去了,搭车回团部,但少年气盛,心想不就16公里吗,没车就不能去吗?我让钉一个木爬犁,给我派一个人,拉着爬犁上路了。走了八公里,才碰到师部的卡车,把我带到了194公里伐木点。当晚放映后,我搭装满8米长大圆木的大挂车回团部。
车下山后行驶到一条河上,结冰积雪的河道很平整,也没有大的急弯。连轴转的司机小肖突然问我:“会不会开车?”“不会,只开过一次东方红。”他说:“道理一样,你看,踩这离合器挂好档后,轻踩这油门加速,再换档,方向盘和拖拉机方向杆一样,路这么好,挂上五档就不用换档了,只管踩着油门顺车辙慢转方向盘就行了,你试试。”说着停下车让我和他换了位置。第一次坐在司机的位置,我并没紧张,按着他的指点踩离合器、挂挡、换档、加速都很顺利,车平平稳稳的开着大灯前进了。行驶十几公里时,他已不再指点夸奖鼓励我,发出了鼾声。
漆黑的夜里,车大灯照亮的白色车辙在延伸,时速已达80公里,我发现速度快更平稳。正在我得意没学就会开车了时,前面出现一个稍急一点的弯,我且不知道减速,顺打方向盘,车头一下扎进了路旁雪堆里,后面的挂车侧翻了,幸好车头和挂车不是一体的,车头没翻。
真是没有天生的英雄,“白马”不是那么好驾驭的。
英雄都是骑马挎枪走天下,马还是要骑的。到五连放电影,雨下了两天也不停,路已经什么车都不能走了,可影片必须送回团部,我准备步行只拿影片回去。老刘牵来一匹高头大马说:“四条腿比两条腿好”,“我没骑过马”,“不要紧,这马老实,不会尥蹶子,平时都不让它跑,只养它膘肥体壮,因为是种马”。我来了兴趣,也想滚鞍上马威风一下,但没有马鞍,老刘说:“不用马鞍,这马走得稳背又肥”。说着把我扶上马背,缰绳放我手里,嘱咐我让它转弯用缰绳,前行用脚和手。我揹着影片,外面穿上雨衣打马出发了。那马果然老实走得平稳,只是像散步,我打两下,它快走两步,然后还是散步,后来更不在乎我的踢打,我行我素了。我想到开车事了,平下心来,慢就慢吧,省得颠簸冒险。可是走了几百米,它且掉头往回走了,我怎么拽缰绳、吆喝都无用。四条腿溜达回了马厩,我还是靠两条腿回了团部。
后来有机会我骑着它“英雄”地拍了张照片,虽然那马是老实站着的,照片背后我还是写了:跃马出征战天涯,壮志未酬不回家。马渴痛饮银河水,我品嫦娥桂花茶。也算圆了“英雄”梦。
那年春节,盼望已久的新片《看不见的战线》年三十轮到了我们团放映两天。电影是那时最重要的文化活动,新片,又是春节,团里重视,派汽车跟随要求全团各连都要看到,可放映员只我一人。深夜的车灯余光经常反射出道旁绿色的亮点,我知道那是野兽的眼睛,在到新建点的路上,车开不快,那绿光竞有数十点,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老司机谭师傅说,那是狼群。两天两夜,汽车司机换了三个人五个班,四十八小时我没睡觉,多次被人叫起换片,我坚持下来完成了任务。
那一年我被评为五好战士,但没发给我“银枪”。
对枪和武器的爱好可能是所有男人的共性,没发给我“银枪”不要紧,我身边很容易摸到枪。一天在保卫股,看到石股长的小手枪和擦枪布放在床上,我想起了儿时自己刻制的木头手枪,那手枪吸引了院里多少小孩羡慕的眼光,还是盒子炮呢。想着,我顺手拿起了床上的手枪,是把撸子枪,好奇的拉了一下,心想,石股长在擦枪,枪里不会有子弹,就举起枪,做出射击姿式,对着门下扣动了扳机,“呯”一声响,屋内几人都惊呆了。幸亏我牢记着小时候妈妈的教导:拿刀拿枪都不要对着人,巧的是那子弹射进了门下基石的缝里,若射在石头上,反射回来,不知伤到谁呢。
“银枪”也不是好耍的。
一个极寒冷的冬天,见赵璐喜劈开一块桦木劈柴时,桦树皮和树干分离后,各有一行字,树干上是凹下去的字,树皮是凸出的字,共十个刀刻繁体字:“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怕被人烧掉,我们珍惜地把它们放到了宣传股小仓库里,我说:“回哈尔滨时,我把它带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去”,就带着《钢琴伴唱红灯记》影片下连队放电影去了。
放映样板戏影片是重要政治任务,无论放映了多少遍,有没有人看,要向上级汇报放映场次,是重要业绩。寒夜,在十三连放映时,大食堂早已没有了窗玻璃,四面透风,我们只能在厨房内,向打饭窗口外放映。来了没几个人,跺脚站着观看。换第二卷片时,我向外一看,观众只剩一个据说神经不好的人和一个几岁小孩了。我感慨,露天放映宽银幕《卖花姑娘》时,开演不久下雨渐大,观众千余,无一人离场。又想样板戏中的英雄是幸运的,虽然今天没人看,但他们家喻户晓。而刻下那十个字的人是不是英雄呢?那时代会写字,至少是生活无忧的人,民族危难时能挺身而出,应该具有崇高的境界吧,“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且无人知晓。
我回到宣传股,去找那两件文物,已经不见了,荒原也有过崇高的证据,不知被谁烧掉了。
“远眺大荒”

地老天荒
当年在曙光农场,跟车去八虎力果园拉沙果,我曾冒失地爬到了几十米高的高压输电塔的分叉处,去俯视大地。感到高度还不够,就向一个几米高的支臂爬去,被尤特司机大夏拼命喊了下来,我才知道那是三十万伏的带电高压线,我险些进入电击场,有些后怕。但多年来,登高远眺北大荒景色的愿望一直在心。
机会来了,师里要办展览,我和吴裕章、孙国平想把团部建设面貌拍下来,寻找了几个拍摄点拍的都不理想。为拍摄全景,我带着相机爬上了三十多米高的锅炉房大烟筒,这个高度在整个抚远荒原也应是制高点了。天上飘着白云,我感到离天那么近,下面很多很小的人都抬头望着我,白云的飘动并没让我感到眩晕,我两腿跨着像脸盆一样大小的烟筒口,沉着地倒举起120海鸥相机,几个方向拍了一卷胶片后,我停留了一会,满足地欣赏到了这个角度的北大荒。远眺那更广阔的视野,展现了平地见不到的壮美画面,蓝天白云,各种不同层次的绿色交错组合,其中点点红色是拖拉机,最美丽的还是阿娜多姿的白桦林,团部的红砖红瓦房也不显得多余,那也是我们征服荒原的成果。
照片拍摄是成功的,我们将五张整幅相纸的照片拼接成一幅六十一团团部全景图,角度新颖。在师部布展时,师长王少伯来参观,离很远就奔过来,嘴里喊着这是哪?
制高点的远眺,加深了我对北大荒博大美丽和神奇的感受,我好像发现了“白马”?
“画坛初探”

我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制作幻灯片,我把王明没有眼珠的漫画头像和眼珠分别画在两张透明胶片上,放映时移动眼珠胶片,影像中王明的眼睛就狡猾的转动起来,会引观众一阵惊奇。
1970年,兵团办第一期美术学习班,要六师去两人参加,说六十一团有个画得好的,就派我和六十团的冯焕山去参加。7月2日到了佳木斯兵团俱乐部报道,方知是为了参加沈阳军区画展而办的美术创作班。参加画展,我并不陌生,小学时就参加过市儿童画展,还得了二等奖呢。领导是兵团战士报报社美编颜红蜀,他曾是上海工艺美校的教师,参加者除两位老同志孔祥生、杨凯生搞过版画创作外,都是第一次搞创作,学员有李斌、陈宜明、赵国经、孙达明、方昉、李可克等19人,冯远拿五幅画来过一次,但没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