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和银枪”---我的北大荒(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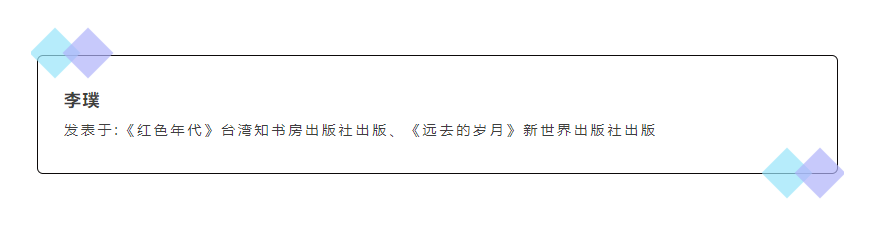
1949年10月1日早4点多,被土改时分光土地没收家业财产后,郁闷成疾的爷爷失望地离开了人间,没能看到一小时后来到人间的我。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1958年的一天下午,哈尔滨的天突然如黑夜般暗了下来,上小学的我抬头一看,满天空悬着无数鸭梨状黑色的云球,很低很低好像要砸下来一样(后来我知道那是梨状云)。面对我的惊恐,妈妈说:“不怕,天塌不下来,来,妈妈接着给你读罗成叫关”,我说:“知道,来的是少年英雄,白马银枪小罗成”(民间词话“兴唐传”中的世家公子,每次出场都是这两句词)。
那一天我知道了自然界的风云多变,不知道的是人间风云同样不测,父亲已成了右派。
“自愿下乡”

天苍苍
1966年就是风云不测的一年。
6月18日,哈尔滨市六十二中学初三第六班的教室传来了读报声,虽是毕业班,但早已没有了紧张的备考复习,说是因教育改革,要取消高中升学考试,应届生何去何从并没有说法。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的两封《致毛主席的信》:“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毕业生先到工农兵中去锻炼,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得到工农兵的批准,取得他们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表现积极的同学升学”。一心想上高中、上大学当科学家(初二就自装过六管半导体收音机)、像哈军工研究生毕业,进军研工作就是少校的表叔那样荣耀的我,非常迷茫。
随着报上社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发表,不知从何处传来了各校应届初中毕业生放弃升学,要求下乡的消息,有的还到市教育局请愿,要求打破只有社会青年才会被动员下乡的惯例。我们全班在也是热血青年,二十五岁吉林师大毕业的女老师章杏瑛带领的讨论中,好像从中看到了天机:将来是要先取得贫下中农的毕业证书才能升学的,早去下乡比晚去好,只要表现好,早去早回,学校不能没学生,得出了做时代先行者,我们也要到农村去的结论。一时群情激昂,纷纷到学校广播室向全校表态,连老师一起全班报名要到农村去,其它班级也随之而起。
激情下我们全班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两个同学把信交给了哈尔滨到北京18次特快列车的列车长,列车长郑重地说:“我们一定把这封信带到北京交给毛主席”。
到红星电影院听曙光农场来的干部黄大忠介绍场况时,大部分同学都因家长不同意而退出了,决心下乡去当一名农垦战士的是我们班15人,全校62人。
不知天高地厚、自认聪明的我,并不只是个表现积极的盲从者,是真的自愿。因为初中一年寒假,每班两个同学作为首批发展对象参加团课学习,我就是其一,但到毕业也没能入团,我知道是因为家庭出身。相信自古英雄出少年,所以从小就想骑白马挥银枪,成为英雄或成名成家的我,就得比别人更革命才能摆脱那个不可选择的出身。
这样的大事,家长哪能让孩子自作主张,那时动员下乡要求家长、学校、学生三同意。奶奶到学校强烈表示家长不同意,父母几乎动员了所有亲属来劝我不要任性,今年如不能升学了,可安排我到军工厂工作等等许愿。我说:“罗成16岁闯关叫阵,我都快17了,该出去闯闯了”,妈妈的最后办法只能每天带着户口本上班了。
迁户口的最后期限那天,我拿着购粮证来到了新兴派出所,两个同学向女民警李燕证明:他家里全都同意他下乡,东西都准备好了,只是今天他忘带钥匙,进不去屋,迁户口的最后一天了,只能拿昨天买粮还在兜里的购粮证来了。
7月12日,没有白马,也没有银枪,我只带了一朵大红花,和165名各校同学一起,做为哈尔滨市第一批自愿下乡的在校初中毕业生站在卡车上,五音不全地唱着“中华儿女志在四方”豪迈的歌,顺着靖宇大街游走,不时见到“欢送知青下乡”、“学习知青革命行动”等标语,从这一刻起,知青成了我们共同的名字。记得路过新华书店时,有人还放过一挂鞭。
滨江站拥挤的送行人群中我只从车窗见到了妈妈和奶奶,其他家人被挤散没有找到我。
“到北大荒”

洪荒初元
13日早上,八虎力火车站,细雨中曙光农场的卡车早已等待,锣鼓声中我们到了场部,三天的参观学习,我并没感到这北大荒有多么荒凉,也没有场况介绍的那么好,先进的农村而已。我只记得我第一次摸到安2型双翼飞机的机翼,惊奇地发现竟是布做的。三天后我们165人分别被分到二队和五队去集训,我到了五队。
五队是农垦部东北局的标兵队,据介绍这里冬天可吃上鲜韭菜和黄瓜,队里青年干部么万和是全国青代会代表,和毛主席合过影,有着出口成章的口才,自然是我们的学习辅导员了。学不断发表的文革文件,十六条等,还有挥舞木棒的练武课,少不了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吃忆苦饭,含泪齐唱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参加第一次劳动是7月18日,大豆地里拔大草。我这一天的日记里记了这么几段话:“今天我们上了到曙光农场以来的第一堂劳动课,拔草这活看起来容易,干起来可就费力了,拔完一垄之后,把我累得直不起腰来……。干完活在地头上我又看了一会主席语录……。劳动途中,我主动要求给全连(队)担水,是抱着为同学服务的思想,可是由于我在家没担过水,这回一走起来可就觉得两臂发酸,压的(得)我走不动了。这时旁边的农工看见了,要我放下他们挑。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话:‘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想到这我浑身就增添了力气,又一口气挑了很远,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吗?”当年日记是我的真实记录,就是那样天真傻气。当年有一个和雷锋并列的英雄王杰,我认为他就是现代的罗成,毛泽东思想就是他的银枪,白马也许就是他成为解放军战士的机遇?向他学,遇什么事都结合毛主席的话去想。他的日记对我很有影响,我也是多记思想,当然是记进步的了,想当英雄、成名成家的想法都是万不能记的,若被人看到,一切努力就都完了。
一天,要收工了,我突然发现随身必带,引为自豪的宝贝,全队唯一的一本毛主席语录不见了,那是在军工厂的老叔给我的,军队系统内部发行的珍贵礼物。全体知青都主动返回田间帮我寻找,虽然没找到,知青们和我一样焦急、关切使我更感到像丢了大家的宝贝一样自责,幸好不久红宝书就满天下了。
每天唱着“咱是革命的庄稼汉……,风吹雨打心里甜那”往回走时,我常想这大热天,同学们且都热情高涨,不论是在大豆地、麦田还是晒场,都不顾汗水、泥土和劳累,那都是在积极表现,要成为其中的罗成,必得有“白马”和“银枪”。
“风云突变”

韶华
8月18日,队里大喇叭传来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激动人心的消息,石破天惊,我们也热血沸腾,高呼毛主席万岁。我心里且感到了失落,我们下乡对不对?在校的同学们已经走到了时代革命的最前线,有点后悔我们过早离校了。
几天后,不知么万和从哪弄来的红卫兵袖章,我们都成了红卫兵,自然要有革命行动了。
一九四八年建场的曙光农场原是劳改农场,不少国民党军的俘虏解除劳改后都成了农工。有人揭发原国军团长李尧周藏有蒋介石的委任状和手枪。我随着大队红卫兵去李家搜查,我没挤到前面,快撤时有机会望一眼屋里,看到火炕已被扒开。
27日,农场唯一的北京吉普车停在了队部门前,带着红卫兵袖章,胸前毛主席像章闪着金光的我们班长刘玉凤和二班的陈邦泰威风凛凛地走下车来,他们是刚从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归来,带着革命任务来接我们回校闹革命的。
28日,场里派大卡车把我们送到八虎力火车站。
学校完全变了样,教室窗户多数已破碎,部分楼道堆满了桌椅,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和各种口号、标语,校长刘树汉被剃了鬼头和于泽、郭振英、张光录等老师,挂着牌子低头站在阳光下。同学间已分为多个相互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和我同在市体操队的一个很老实的队友,成了一个很有实力组织的头头,两腿放在桌子上,斥责下属革命不彻底,我知道了“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语义。
各组织都忙于互相争斗和大串联,刘玉凤也不知哪里去了,我们被边缘化了。父亲是右派的我,不能参加大串联,更不敢“闯关叫阵”,但也没只是观望,我画过漫画、刻过钢板、印过传单。
9月,知青领队李江华传来农场正在秋收,人手不够,希望我们回去的消息。当月正无所适从的我们又都回到了曙光农场,这回我们被分到了各生产队,我们十二个知青分到了曙光四队。
“一列火车”
寒冬修水利,用拖拉机大犁把冻土翻过来,人工把大土垡子块揹到挖好的沟旁筑成土坝。这活很累,17岁的我揹着沉重的土垡子有时会觉得眼前发黑,咬牙坚持的同时还不忘宣传员的职责,大声背几句毛主席语录或自编的顺口溜。开饭了,工地吃得好:热腾腾的长形白面馒头,大米稀粥,猪肉粉条,那馒头暄得放到嘴里几乎不用嚼就可咽下去,大家数着数吃,我一口气竟吃了十六个馒头和五碗稀粥,书记纪振起说:“你那十六个馒头摆在一起是一列火车了”。我心想,“来的是少年英雄”嘛。
我到四队时身高1.74米,再回家时,长到了1.77米,和这一列火车不无关系吧。
“舞台风光”

雁过留声
多才多艺的文书孟宪德带领排小歌剧,让我演男主角解放军,穿上军装,系上转业军人用的宽宽的八一军用皮带,还插了一把道具手枪,好一个“白马银枪”,我感觉很风光。可那几句唱词“离别家乡十八年,今夜重返八宝塞……”我五音不全又没节奏感怎么也唱不准。大家哄堂大笑后,二胡伴奏高汝庚、女角孔祥琴、张凤英和孟宪德都耐心地教我,还打着竹板纠正我的节奏感,我且离了竹板的节奏就还是原样。无奈只得让我去和林景义同演台湾潜入特务金包铁银包铁了,一上岸就被解放军和男女民兵抓住了。只一句唱词“老鼠爬竹杠,越爬心越跳”而且唱不准也不怕,因为是反角,但已不风光了。
虽然到场部汇演时,我参加表演的对口词反映还是不错的,但我还是知道舞台不会成为我的“白马”了,音乐也不会是我的“银枪”,从此,总拉不出准调的二胡再也不拉了。
“狂涛再起”
文革逐渐向高潮发展,到场部参加文艺汇演的知青们交流的各种消息中:说是鼓励批准我们下乡,是反动路线为了分散革命力量的大阴谋,各农场知青都回城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任务了;哈市已经成立了返城知青造反团,就缺我们农场知青的两条消息,让我们决定行动了。
1966年12月27日,寒风中,毛广芬、白昉、邢继宽等,我们四十人登上了开往哈尔滨列车的一节闷罐车。全国大串连正在高潮,乘车不用买票,但人很拥挤。
省委安排我们住在和平电影院旁做为省委招待所的黑龙江旅社,这里就成了我们造反分团驻地,姜志敏是头头之一,不知他从哪弄来的面包、汽水,有吃有喝还能住。我发现一个房间里有一个老干部皱眉来回走动,别人告诉我,他是副省长孙希奇,几个造反团的人都在抢他,我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官。
返城知青造反团的主要目的是要把户口迁回哈尔滨,真正和留校同学们一样闹革命。一个夜晚,头头叫我们去文化宫。舞台上全是我们返城知青造反团的人,中间几张椅子上坐着我们的几个头头,正和被批斗中的省委常务书记任仲夷谈判。夜11点多,终于迫使任同意发文件将知青户口都从农场迁回哈市。怕其有变,让任马上调动人员打印文件,并看着他们把红头文件封装,送到邮局发往各农场,各农场代表也各拿了一份,欢呼胜利后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就开始有人回农场了,很快传来消息,回农场的人并没有如愿迁回户口。原来农场接到给知青迁户口文件的几个小时后,又接到了不许给知青迁户口的文件。据说只有某农场的两个知青,拿着文件当夜乘火车返回农场,成功地把户口迁回了哈尔滨,我知道了时机和成功的关系。
这次行动后,返城知青造反团基本上没有了集体活动,成了散沙,“英雄”们都没有了用武之地。
文革高潮中我们都成了无所属的逍遥派、观望者。我目睹了老字号同记商场被涂成了红色、哈一机军工厂的坦克开上了大街、同院很受尊敬的大家族苗家,慈祥健康的大爷大娘被街道红卫兵,两天内相继打死……。
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无着落的我们又都分别回农场了,我也回到了曙光四队。
“更夫好梦”
曙光四队也不是一片净土,回来的第二天早上去食堂,外面站着挂牌子的反坏分子,其中竟有一个和我同时分到四队的知青,他善说,哪句话说错了吧?我更得谨慎。
派我夜班看管杨傻子,因在大家恭请毛主席像时他说了:“和请灶王爷一样”,而成了现行反革命的贫农。每晚六点半我到他家,把他押到队里一个窗被钉死的小房间,门上锁,吃完夜班饭再去开门放他出来解手,早六点半再押他回家吃饭,我一天的工作完成。几天后他和我说:“晚上不起夜了,你不用来了”,我后来发现他都尿到炕洞里了。这位现行反革命也就这么大能耐,还有比他更傻的吧?
可能看我体弱,麦收时队里又安排我打更,和老光棍刘传祥看场院,上半夜常在老刘的指点下去弄点鲜瓜果,吃完夜班饭,老刘就让我在库房空麻袋上去睡,白天逍遥自在,还有机会去附近的三河屯买东西,老刘说:“打一辈子更睡两辈子觉”。一天夜里,我正做着骑白马,耍银枪的好梦,孙延光队长来取我身下的麻袋,把我拽醒。我想这下坏了,队长肯定批评我,不会让我干了,第二天什么事也没有。
其实那是一种关爱。
“指路进山”

大漠孤烟
上山伐木出发前,出纳高汝庚说山上冷,雪深,得扎绑腿。 高教我扎绑腿,我总是扎得太松,后来他亲自帮我扎好,那专注、真诚和温暖至今在心。
